进入新的BBIN入口世纪,当今中国人文科学面临新的挑战,也形成了BBIN官网新的机遇,人文科学重新登场的呼声愈来愈高,那么,中国人文科学的现状与未来究竟如何?
该人文学者登场了吗?
对这三十五年来的中国学界,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,如要更精准加以深描,大体可以这样爬梳:80年代乃启蒙时代,人文科学充当了引导者角色,直到市场经济建立之后,以经济学为主的社会科学才开始位居主流,同时,人文科学的确退居到了边缘,当时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就是对此思想界变动之反应。遗憾的是,作为“赛先生”的科学传统却始终没有扎下坚实根基,起码在民众当中自然科普读物如脑科学、动物行为学、生态保护之类,就没如欧美那样成为畅销书过,还有《新资本论》这类被《纽约时报》称为“21世纪新版的资本论”的经济学著作。我们现在遭遇的问题是:自然科学尚无深根,社会科学无法有力地阐释并引导经济政治发展,人文科学难以为中国人提供民族精神的支撑,那么,当代中华文明的思想内核到底何处寻?
如今,恰恰要在自然、社会与人文三种科学之间,重新找到一种新的动态平衡,人文科学的复兴要在三种科学的谐和当中才更有意义,事实上,人文在当下中国也在复苏进行时。近期邓晓芒提出的观点我是赞同的:要从德文Wissenschaft的广义上而非英法的science狭义上理解科学,由此可分殊为“小科学”(即数学与自然科学)、“中间科学”(即社会科学)与“大科学”(即人文科学),这大致不错。但他进而认定,不是自然科学为人文科学奠基,而是人文科学为自然科学奠基,却有失偏颇。事实上,人文学者和科学家之间的“两种文化”断裂的所谓斯诺命题,恰恰可以通过人文与科学相互奠基的方式来解决,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张力也可做此解。
这就涉及到当今国际思想界所倡导的“后人文主义”(Posthumanism)新潮,这种“后人文主义”恰恰结合了人文与科学的新趋势。为什么这样说呢?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,如DNA与现代生物科技、神经元网络与电子思维的发展,人性本质也在被逐渐改造,这种非进化论的趋势曾被叫做“跨人文主义”(transhumanism)。这种“跨人文主义”作为从人类到后人类的某种中间状态,它的最新走势乃走向了“后人文主义”,当今中国人文科学的复兴却可以追赶上这个国际前沿,因为中国原典思想家早就在人性论的——自然生成与人文化成——之间寻求到了中道之处。由此,中国的人文科学也可就此返本开新:它既是全球的,也是本土的。
其实,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有着不同的逻辑。邓正来先生所倡中国社会科学的“自主性”,仍是建立在“合法性”(Legitimacy)基础上的:本土经济学、政治学要为中国模式提供理论模型,这都需要合法性论证,但中国模式是否是对普世价值的对抗,改革开放是不是摆脱中国模式的历史过程,如今都没有论辩明白。与社会科学的合法性基础不同,中国人文科学则亟需“自创性”,而这种自创则是建基在“合理性”(Reasonableness)根基上的。社会科学亟待合法性证明,人文科学则必需合理性论证。从长远角度来看,中国人文科学能为这个全球世界所提供的,势必要比中国经济模式抑或政治话语所能提供的,更具深广影响与全球价值,中国人文主义需要且正在复兴挪威对决拉脱维亚:东风压倒西风?!
“东风”压倒“西风”?
所谓“东风”压倒“西风”,这个提法本身就是民族主义式的:曾经挪威对决拉脱维亚:东风压倒西风?你BBIN平台压到我,未来我压倒挪威对决拉脱维亚:东风压倒西风?你!建议应用和而不同式的那种均衡语汇来形容这种未来的关系,但即使是东西方真正能势均力敌,也要假以时日,许多人认为至少要等一百年,但如今则是“东方既白”的时候了。季羡林先生曾有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的论断,认为西方之“分析”传统已到穷途,后三十年就要靠东方之“综合”来领风骚。无论这种东西比较是否合理,这个历史周期都要划得更长一些,起码要再等一个甲子六十年,中国才能从西方那里获得应有的话语权:革命尚未成功,同志仍需努力。
如今的现状仍是欧美学术占全球霸权,中国学术则刚在全球语境内兴起,但仍囿于中心与边缘的结构。这种等差结构就决定了,中心看不到或不用看边缘。汉学仍是西学的边缘学科,汉学家在外冷清在国内却热闹,道理很简单,因为人家是研究你的嘛。然而,边缘却时时看着中心,我们始终在向外看,并潜意识地以中心作为标准,所以本位论者疾呼该是抛弃西方的时候了。汉学的由外译中,与中学的由中译外,也形成了巨大的贸易逆差,但是如何转为顺差?在国际学术舞台上,我们的影响力远远小于更早学欧美的日本乃至直接说英语的印度,尽管这种情况在新世纪以来得以某种转变,各种国际会议在中国纷纷召开,但背后所支持的却不只是学术的累积而是经济的坚挺。即便如此,什么世界学术中心的东移之类的判定,恐怕也只是否来自东方的想象与幻觉而已。
问题就在于,我们现在能彻底抛开西方来“说事”吗?80年代的西化思潮尽吹,90年代则是保守主义回潮,如今则是更混杂的历史局面。所谓西学话语受挫的判断,这只是基于当今中国的表面状况,但事实是,我们这一百多年的学问就是从学习西方开始并由此形成了“中西视界融合”。我们始终都介于中西之间的,不信把我们研究的基本语汇与关键词汇通通拿掉,进行一番现象学还原,看看还剩下多少我们自己的话语?因为我们就是在现代汉语所新构的语言体系当中来进行学术建构的,这里就有一个从 × × 学问“在中国”到“中国化”的× × 学问的问题,这个× × 基本上都是来自西方的学术建制,而不是本土化的经学之类。所以说,东风的兴起,不是大势所趋,而是小势所趋,我们才见东方既白,但是一种古老而青春的力量却彰显出来。
至于儒家是否能回归政教的中心,显然众说纷纭。我们起码可以区分出事实与价值判断两类:事实上儒家尚未回归政教中心,尽管儒家在价值上力求实现这种回归,但事实与价值恐怕是两码事,这是其一。其二,儒学当然可能成为主导,从独尊儒术至晚晴衰落大抵如此,但是即使成为主导,这个主导到底是要回到“道统”继续统领“政统”及“学统”,还是回归更为普遍的民众日常生活,这需要历史来给答案。其三,即使儒学再成一统,这种一统也不是“大一统”,因为历史上的儒家皆要与道家形成互补,吸纳佛教的要素,并兼及墨法等智慧,从而能形成中华民族思想的整体健康谱系。
形势大好还是问题重重?
当前的人文学界,仍面临着问题重重,重重问题!表面的繁荣对应着内在的贫乏,真不知该从何谈起,我只知道,其中最关键还在创造,就在创造。鲁迅先生在1934年就曾问到: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?如今的我们显然不乏自信,却失去了创新的能力,我们要再追问——难道中国人失掉创造力了吗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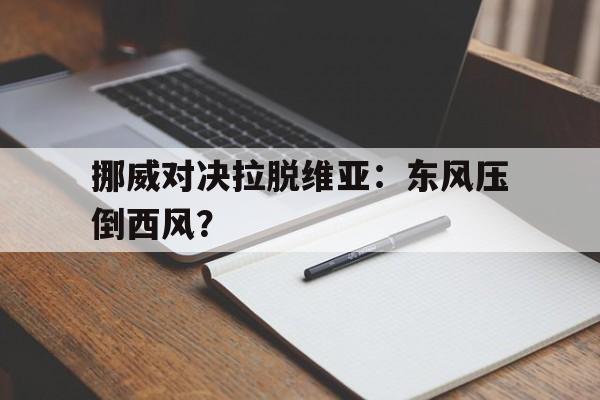
欧美人文学术之所以能够引领全球思潮,成功之处就在于其创造性。没有创造性的学术,只能成为本土思想的重复者,抑或外来思想的模仿者。所以说,如何实现中国人文科学的创造,才是问题核心中的核心。林毓生先生提出“创造性转化”与李泽厚先生提出“转化性创造”皆致力于此,前者重转化,后者重创造,后者较之前者更强调不以“西方现成的模式作为模仿、追求与转换的对象”,而是根据中国自己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创造出一些新的“形式与模态”出来。这种转化,无论是针对本土传统还是外来资源,其中的关键都在创造:有了创造,才有转化;转换成功,就是创造!
当然,只有创造了,才是自己的,所以我才称之为“自创”,也就是创造自我。这里的“自创”起码包涵两个涵义:其一就是自我的“创新”,其二则是自我的“创生”,前者说的是富有创造力的新构,后者则是说具有持续力的拓展,二者缺一不可,既要真有创新又要创新持久。“京都学派”便是如此,以西学为视角、以东学为对象,学术新创而又有几代传承,进而形成了包含文史哲的综合学派。我们民国时期的学术就具有自创性,在学术初创时期总会有青春活力 ,即使80年代也是产生经典的时代,如今的最大问题则是创新意识不足,但又盲目新创,所以只能创造出大量重复的学术垃圾,这是我们有目共睹的。
与创造力的丧失相关的,乃是创新标准的失范。这种标准决定了何为创新,反过来也决定了什么不是创新?这种标准如今尽管要以全球性为坐标,但同时又要具有本土性,它仍是中国自己的标准。这种标准尽管直面各种话语分裂的当下格局,但是仍是要具有公约性而相对公正的,它要在多元性寻求新的统一。但即使这个标准问题解决了,更难的还在如何创新?人文学者们要更善于发现创新中的真正问题,更善于解决创新中的真正难点,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之后,人文科学的”自创”才会水到渠成吧!
新增长点与突破点在哪?
当今人文学术的新生长点,这是个正在将来完成时的大问题,但还是可以做些预测,只能根据自己的观感说一些,也只就文史哲三个基本学科来说,仅代表个人意见而已,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。
在哲学上,哲学成为“生活之道”已成为当今全球哲学的最新发展趋势之一,哲学不应只被当作理论学科,在雅典举办的第23届世界哲学大会的双重主题“审问明辨与生活之道”即为明证,在北京举办的下一届哲学大会的主题也是“学以成人”。在走向生活的哲学道路上,“情感哲学”应该是其中的重要路径,近十年来欧美情感哲学变得相当发达,而这种既重情又重理的思路中国古已有之。这种哲学新思路,力图超出西方哲学的“理性中心主义”、“逻各斯中心主义”、“欧洲中心主义”与“男权中心主义”,对于全球哲学的整合而言意义重大。当今的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也已出现了所谓The Affective Turn抑或Emotional Turn,也就是感受论转向抑或情感论转向,因为这种感受跨越于心灵与身体、行动与激情之间,从而以一种综合的视角使得“社会理论化”,由此变成了欧美学界的新热点。
在文学上,文学研究大致分为史论两类,文学史研究的亮点此起彼伏,而当今文艺理论的最新趋势乃为文学回到生活:这不仅是对当今“微时代”的文学命运之深描,也同时是对文学本身的一种理论诉求,它要求回到“生活美学”来规定文学的本体存在。因为文学既是生活又是审美,既是一种生活形式,也是一种审美方式,这两面恰是合二为一的。在近十年的文学研究中,“文化研究”曾渐成主流,如今则显衰颓之势,视觉文化研究也终未成势头,但是诸如“后女性主义”尚待发掘之中。在2007年出版的英文文集《感受转向》当中,就说近十年来学界就犹如当年的语言转向和文化转向一样,如今情感或感受转向则渐成大势,体现为一面是在女性主义理论里的身体研究,另一面则是在酷儿理论当中的情感研究,这些无疑都是新颖的。
在历史上,有两种趋势值得关注。一个是“全球史”与中国史的关系,中国史要被置于更广博的世界语境当中来考量,比如中国的海洋文明及其历史就值得关注。笔者在纽约做富布莱特访学之际,与哥伦比亚大学莫里斯·罗萨比(Morris Rossabi)教授深有交往,他曾有两本大著《中国与内陆亚洲》和《中国及其邻邦》,并在2013年写了一本《中国史》,特别是那本《来自上都的行者:拉班-扫马和马克西行记》,说明这中国许多朝代对外并不如传统所认定的那般孤立,而常是平等地对待外来人士的,那种黄色文明的封闭性也非实情。另一个则是“文化史”与“生活史”的研究,不仅历史研究的对象从精英下降到下层人,而且性别、种族、新族群等研究得以拓展,特别是超越了社会史研究的“新文化史”蔚然成风。这些新视角都值得移植到历史研究当中。比如“新清史”之争就折射出反汉族中心主义的种族视角,但中华的“民族性”到底是种族还是文化概念仍值得商榷。但无论文史哲的研究如何得以新拓,学术与思想都是不可分的,这不禁令人想起王元化先生当年的呼吁——要做“有学术的思想”与“有思想的学术”!
(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)
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,不代表XX立场。
本文系作者授权百度百家发表,未经许可,不得转载。